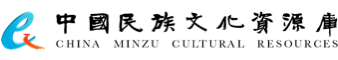
洞经音乐,是广泛流传于云南民间的一个音乐品种,历史悠久,深受云南各民族广大群众所钟爱,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云南卷》收编范围;1984年收入《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近40年来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迄今为止,有关研究文章不下500篇,各种观点令人目不暇接,莫衷一是。为此,记者采访了对洞经音乐研究已有57年的吴学源,他曾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云南卷》主编,是我省资深的音乐学家,现仍笔耕不辍,还在对云南各民族民间音乐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现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顾问(曾任副会长)、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仍在为云南省的“非遗”保护工程孜孜不倦地工作。随着吴老的认真讲解,这个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古老音乐,展现出不一般的魅力,它不仅仅是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存在,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文人身份的象征,代表着儒家礼乐艺术成就的荣耀。
今天就由民族音乐学家吴学源带您一起揭开古老洞经音乐的神秘面纱,领略450多年的儒家礼乐。
民族时报:请问吴老师,什么是洞经音乐?
吴学源:《洞经》,是一部经书的简称,全称是《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唱诵这部经书中“诗、赞、咒、偈”的音乐,就是“洞经音乐”。
民族时报:有人解释这部经书的名称,说是从山洞里拿出来的经书,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吴学源:山洞里拿出来的经书?(笑)这是望文生义,不恭敬地说这是“忽悠”。这部经书的内容很丰富,首先要说“文昌”的含义,文昌指的就是文昌神,“文昌”本是斗魁六星的总称,民间也称为“文曲星”或“文星”,古代传说是天上主宰文化教育的星宿;而“文昌帝君”,则是元代元仁宗诰封出来的一位俗神,原型是晋代四川梓潼县的民间传说人物张亚子,后来被当地的老百姓追奉为七曲山的土地神,至今也还被当地视为驱瘟的神、蛇神。宋元时,四川道士为了把这一位地方神纳入到道教的神灵体系中,便以扶鸾降乩方式宣称玉皇大帝已将梓潼神封为“文昌帝君”;为了说明封赠原由,还编出了叙说梓潼神圣迹的《清河内传》、《梓潼化书》。到了元代延祐年间,四川卫姓道士上书朝廷,请求将这位土地神诰封为文昌帝君,此事曾引发朝廷辩论,许多大臣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最终元仁宗还是正式诰封了这位土地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辅元”即辅佐元朝;至此,梓潼神与文昌星合二为一,成为主宰人间科举文籍、官禄爵位的大神。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文人一再上书朝廷,希望罢免梓潼神的文昌帝君称号,提出在各地学校中的文昌祠(阁),都应该拆毁。直到《清河内传》、《梓潼化书》以及相关的两部“文昌大洞仙经”收入到明《正统道藏》后,经明英宗御批诏颁全国,这些争论才逐渐平息淡化。之后,在朝廷的倡导下,文昌神逐步得到士子文人的认可,从明代中期开始,为了科举仕进、升官进爵,儒生们开始对梓潼文昌神进行典礼膜拜,到了清代日趋兴盛。
民族时报:这部经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吴学源:称为“文昌大洞仙经”的经书不止一部,有好几部。先说一下最原始的一部,叫做《上清大洞真经》,也称为“三十九章经”,这是一部道教上清派修炼内丹的丹经书,是由晋代女道士魏华存传下来的。到了南宋时期,四川刘姓道士将《上清大洞真经》纂编后更名为《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民间简称为“太上本”,共五卷,称为“文昌”的经书是从这里开始的;元代延祐年间,四川卫姓道士又将经书重新改编后命名为《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民间简称为“玉清本”,共十卷;这两部都是道士在静室里修炼内丹的丹经书,文字晦涩隐秘,常人很难看懂其中的内容。主要是说:修仙了道的这部秘籍是原始天王说的,因为传承的时间久了,错讹很多,现在由文昌帝君来重新进行阐释。里面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现在大家所熟悉的气功修炼的导引法和观想修持法,诸如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以及大小周天之类。
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开始祭拜文昌神,于是又根据《正统道藏》中的“太上本”和“玉清本”,再改编出了一部称为《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的经卷,民间称为“太上玉清本”,共有三卷,这就不是修炼内丹的秘籍了,而是一部仪式经卷,称为“醮仪经”,是专门供祭祀礼拜文昌神用的,云南洞经音乐最初谈演的就是这一部,洞经音乐的产生严格说来时间上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的文章把谈演洞经音乐的源头推到元代、南宋、甚至晋代,那是经书的源头,经书不等于音乐。再补充解释一点:“大洞仙经”这个名称,“洞”是通达,“经”是“路径”,意思就是通往神仙道路的秘籍,不是从山洞里面拿出来的经书。
民族时报:最近查阅了许多文章以后,包括网上的大量文章,发觉对于云南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众说纷纭。从时间来看,有“源于春秋,盛行于唐、宋、元、明、清说”,“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说”,也有“唐宋时期说”、“南宋都城临安说”、“元代始于龙门派祖师丘处机说”、“明代永乐七年从梓潼传到大理说”等等,似乎越古越吃香。从地点来看,有“川西道教音乐说”、“梓潼七曲山洞经音乐说”、“北京(或南京)宫廷音乐说”、“明代洪武年间南京移民说”,真是不胜枚举。关于其音乐属性,有“道教音乐说”、“三教音乐合一说”、“江南丝竹说”、“宫廷音乐说”、“儒家礼乐说”,真是热闹非凡。请您谈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吴学源:我坚持的就是儒家礼乐说。30多年来,我在主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云南卷》的过程中,大凡一种新观点出来,都要密切关注,认真求证,不敢有任何疏忽和遗漏,因为我们编纂的是“官修”志书,不是编野史、稗史,不是个人专著;这个求证过程很漫长,也很艰辛,需要去伪存真,以事实说话。当排除了许多至今没有能拿出确凿证据的观点后,历史面目逐步清晰。
关于云南洞经音乐的历史渊源,首先要从经书上去探讨,前面在介绍经书历史时已经涉及到了,其次是从各地洞经会组织的历史来考证。可靠的口碑材料是:嘉靖晚期至隆庆二年(1568年)间,大理到成都做生意的两个儒商得到了《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这个新版本的经书后,带回大理开始依此祭拜文昌神,用当时文人吟唱诗词的“诗曲词调”来诵唱经书里面的赞颂词,逐步形成为规范的礼仪后,被人们称为“洞经音乐”;并组建了云南的第一个“洞经”乐社组织,叫做“桂香会”。多年以后的明朝末年,这种祭典仪式和音乐唱调,被大理到昆明经商以及科考的文人带到昆明,也组建了一个称为“桂香会”的洞经会,这是昆明的第一个洞经会。
康熙九年(1670年),昆明大旱,连续几个月不下雨,不要说庄稼无法种下,就连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当时,老百姓村村寨寨在求雨,道教、佛教等宗教也举行大法会在求雨,可是叫天天不应,求神神不灵。这时昆明桂香会的文人们也想去求雨,但他们只会谈演《文昌大洞仙经》,不会做求雨的法事,怎么办呢?那就谈演《文昌大洞仙经》试试看吧。于是他们就到了北郊黑龙潭,把洞经音乐奏响了,谈经快结束时,远处的天边开始涌起了乌云,到结束时已是乌云遮了半边天;大家眼看大雨就要来临,便匆匆忙忙坐上小马车赶快打道回城,才离开黑龙潭一半路程,刚要过盘龙江上的一座石桥时,狂风骤起,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就下来了,旱情终于得到了缓解。时任云南布政使、官至二品的王继文迅速奏报朝廷,文人求雨灵应的事震动朝廷,康熙皇帝龙颜大悦,挥御笔写下了“霖雨苍天,保黎民众庶”的题赐,自此洞经会名声大振。康熙御笔被刻成匾后悬挂在昆明北郊黑龙潭黑龙宫,后毁于咸同兵燹;那座石桥,被取名为“霖雨桥”,现在新建的霖雨桥仍在北市区盘龙江上,当年的小马车路如今扩修成了“霖雨路”。之后又由桂香会派生出了“保庶会”,“保庶”和“霖雨”,都是来自于康熙皇帝的御题。
吴三桂三藩之乱后,社会逐步稳定,洞经音乐经过自身的不断完善,逐步成熟定型,在官府的支持下,在科举制度的驱使下,从康熙晚期至雍(正)乾(隆)年间,开始在云南各地传播。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们的调查材料证明,最初是传入到汉文化比较发达、有了“士”这一个阶层的一些县城,如新兴(今玉溪)、通海、新平、建水、蒙自、开远、泸西、易门、姚安、保山、腾冲等地,且当地的第一个洞经会都称作“桂香会”。那时我们调查资料的可信度较高,老艺人们不会胡吹乱说。
大约在乾隆晚期嘉庆初年,据说当时被官府通缉的、从内地(省外)逃来的“天地会”钦犯二人被大理桂香会藏匿,事情败露后天地会钦犯及桂香会的三个主要负责人被官府处以极刑,大理“桂香会”自此消失,只留下了口碑传说。这也是昆明“桂香会”后来改名为“桂箓学”、又再改回“桂香学”的隐秘原因,其真相一直讳莫如深,不为世人所知。有的地方的第一个洞经会为什么又称为“桂箓学”、“桂香学”呢?如会泽、曲靖、陆良、师宗等县,这估计是“天地会案”后,才由昆明传过去的。这些称谓,孤证不立,从时序上可以互为印证,互相补充,它为梳理云南洞经音乐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坐标。所以,在探讨云南洞经音乐历史的过程中,我坚信“礼失求诸野”,时间虽然可以抹去许多历史痕迹,但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当我们把这些历史碎片拼接起来后,就找到了云南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和传播的基本脉络。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但我们可以接近历史的真实。
出处:云南民族网(原来源:民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