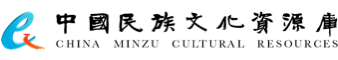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与周边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唐朝国防力量的消弱,河隍州县先后失陷,长安也不断受到吐蕃的威胁和进攻。但经过肃、代、德宗时期的不断调整变化,到宪宗时期,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逐渐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边疆地区的稳定以及来自周边威胁的减少,使唐朝能够集中力量整顿内部事务,裁抑藩镇势力。
一、安史之乱后的民族关系
唐朝前期国力强盛,国内政局稳定。据《通典》记载开元时期盛况:“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唐在周边地区设置都护府,派遣节度使镇守边疆,有效地维持在西北区域的统治和边防的安全。当时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是东北地区契丹;北部地区是突厥,突厥败亡后,回鹘控制漠北地区;西南地区主要是吐蕃和南诏。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抽调河西、陇右等镇军队镇压叛乱,致使“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乾元(公元758-760年)之后,吐蕃乘机占领陇右、河西,后又占据北庭等地。唐鉴于自身所处危势,为避免内外交困,肃宗时期不得不实行妥协政策,姑且接受这一现状。此后,吐蕃国力处于巅峰状态,屡次寇掠边境,甚至威胁长安、京畿地区。代宗、德宗时期,唐与吐蕃关系最为紧张。尤其是贞元三年发生的“平凉劫盟”,使双方不再信任,和平会盟长期难以实行,唯有兵戈相对。
回鹘在灭突厥以后,势力一度强盛。但在天宝以后,唐与回鹘总体保持友好关系,受到唐的册封。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肃宗征回鹘兵,收复两京。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再征回鹘兵,平定了安史余部。同时,唐对回鹘实行和亲政策,并进行绢马贸易,双方关系密切。此间,鉴于唐国势衰弱,回鹘有“轻唐之色”,在唐屡有不法行为,加上马价等贸易问题,关系逐渐发生微妙变化。大历末期,回鹘与唐交恶,侵犯太原。德宗即位后,回鹘亲唐派宰相顿莫货达干夺得回鹘可汗之位。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唐以咸安公主与回鹘和亲,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贞元六年,吐蕃联合葛禄部落,攻陷北庭,对回鹘造成了严重威胁。回鹘不得不把西北的部落迁到牙帐之南。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回鹘和唐联系更加紧密。
开元后期,皮逻阁被册封为云南王,并在唐支持下,统一了六诏,迁居大和城。天宝九年(750年),云南太守张虔陀因问题处理不善,南诏出兵攻杀张虔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出兵大和城,全军覆没。天宝十二年,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再征南诏,大败。不久爆发了安史之乱,云南王阁罗凤乘机攻陷雋州。南诏与唐交恶,因此归附了吐蕃。但是,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引起南诏不满。大历十四年(公元766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即位,在清平官郑回劝说下,决心重新归附唐朝。这一时期韦皋任剑南节度使,实行招抚政策。经过几年酝酿,贞元十年,南诏在苍山神祠,与唐会盟,并且“斩吐蕃使数人,以示归唐”,彻底与吐蕃断绝关系。从此以后南诏重新与唐结盟,共同对抗吐蕃。
贞元前期,回鹘与唐密切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南诏重新与唐朝恢复往来。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消弱,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又受到吐蕃频繁侵犯,也希望联合回鹘、南诏来牵制吐蕃。回鹘本身受到吐蕃威胁,与唐联合可以得到经济上利益,也支持唐朝对抗吐蕃。南诏与吐蕃发生矛盾,重新归附唐。唐与回鹘、南诏的联合,有效遏制了吐蕃的进攻。到元和时期,吐蕃国力趋于衰落,内部不断发生权力纷争,唐朝西部边境出现久违的宁静局面。这些都为唐朝平定藩镇叛乱提供有利时机。
二、元和时期民族关系
宪宗元和时期,唐朝经过两税法改革以及刘晏等人整顿漕运,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与周边民族关系也得到改善。
吐蕃长期威胁唐朝西部和西南地区。“平凉劫盟”后,唐朝加强在西部地区军事布防和攻势。唐德宗接受李泌建议,“北和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在西南地区,剑南节度使韦皋招抚南诏及其他南方诸族,重创吐蕃;西北地区,联合回鹘共同抵御吐蕃。吐蕃虽然在西域地区取得优势地位,但是穷兵黩武,加剧内部矛盾,不得不寻求与唐朝改善关系。贞元十三年(797)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卒,次年,墀德松赞立。墀德松赞期间启用僧人参政,“称钵阐布”,地位很高,主张与唐讲和。贞元十九年五月,吐蕃遣大臣论颊热来唐。唐朝也派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伾出使吐蕃。唐蕃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元和时期,双方基本处于和平状态。虽然相互防御,但军事冲突大大减少。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放归吐蕃俘虏十七人,向吐蕃释放出友好讯息。吐蕃也作出了回应,同年六月派遣论勃藏出使唐。但是双方必须得面对一个历史问题,既“平凉劫盟”的遗留问题。“平凉劫盟”中唐很多官员被劫持到吐蕃,一直未放归。被劫持的副元帅判官路泌之子路随力争要出使吐蕃,“五上表,诣执政泣请”。元和四年,吐蕃请修和好,宪宗派遣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并带有《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元和五年五月,吐蕃派遣论思邪热出使唐,并归还路泌、郑叔矩的灵柩。唐认为吐蕃要诚心修好,需要归还秦、原、安乐三州,“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疆界。”。六月,宰相杜佑与吐蕃使臣就此事进行讨论,但并没有达成协议,因此也没有举行会盟。期间,除元和七年吐蕃寇边外,唐吐基本保持和平状态,甚至在元和十年,吐蕃与唐在陇州关塞处进行互市。这种和平状态维持到元和十三年。在这一年,吐蕃大举侵犯河曲、夏州、盐州等地。十四年,吐蕃再次进攻庆州、盐州。但战事很快结束,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吐蕃与唐结盟,史称“长庆会盟”,结束了这种敌对关系。吐蕃最终因内部分裂而衰弱下去,不再对唐构成威胁。
总体来看,宪宗朝对吐蕃采取防御政策,尽量维持边境稳定。而吐蕃由于连年战争,加上内部矛盾,军事力量转衰,也有意与唐讲和。墀德松赞(公元798-815年)重视佛教而抑制当地本教,改善唐蕃关系。贞元二十年(804)四月,吐蕃派遣使团来唐,包括有僧人。僧人娘定埃增、钵阐布允丹都主张与唐修好。唐朝称赞钵阐布允丹“忠信立诚,
故能辅赞大蕃, 飘和上国……思安边陲, 广慈悲之心, 令息兵甲, 既表卿之远略”。就宪宗朝来说,其主要解决内部藩镇割据问题,加之国力有限,主、客观上都要求采取和平手段。另外,考虑到,“自异牟寻归国,吐蕃不敢犯塞,诚许盟,则南诏怨望”。因此,采取这种“和而不盟”的策略。至于元和十三年、十四年的战事,笔者根据有限的史料推测有以下原因:一、元和十年(815)吐蕃新赞普墀祖德赞立(汉史料称为可黎可足,或称为彝泰赞普),权力的变化可能引起吐蕃对外政策的暂时变化。二、吐蕃一向忌惮唐与回鹘联姻,如长庆元年,“吐蕃犯青塞堡,以我与回鹘和亲故也”。元和十二年,回鹘请和亲,宪宗派遣宗正少卿李诚出使回鹘,本想延缓和亲日期,但此举可能引起吐蕃误会与猜疑。三、元和后期,宪宗有意恢复河陇,边将意欲立功,导致边境地区发生摩擦。
元和时期,唐与回鹘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当时回鹘信奉摩尼教,宪宗于元和元年,根据回鹘建议,允许在长安、凉州、荆州、洪州等地建置摩尼寺。但在和亲问题上,宪宗则犹疑不定。元和三年,咸安公主死于回鹘,回鹘想再和亲,宪宗因忙于平定叛乱藩镇,财力不足,屡屡要求暂缓和亲。李绛建言,“今江、淮大县,岁所入赋有二十万缗者,足以备降主之费。”因此,宪宗不愿立即和亲可能不仅是因为经济原因。回鹘此阶段与吐蕃争夺西北统治权,关系紧张,时而会有战争,元和八年“回鹘发兵度磧南,自柳谷击吐蕃”。笔者以为,元和时期唐与吐蕃关系缓和,难得处于和平状态;此时,回鹘与吐蕃关系紧张,时有征伐。宪宗如果与回鹘进行政治意味浓厚的和亲,就不得不考虑到吐蕃的感受,因此显得十分谨慎。此外,唐虽然与回鹘关系友好,但由于国内正在进行平叛战争和游牧民族漂游不定的特性,在战略上仍然会对其进行防御。元和九年,在宰相李吉甫的建议下,唐设六胡州,以备回鹘。
南诏重新归附唐朝以后,唐对南诏行使册封之权。贞元十一年,德宗曾赐异牟寻“贞元册南诏印”。元和年间,双方往来频繁。元和二年,唐授予南诏使者邓傍试殿中监;元和三年,异牟寻卒,唐派遣太常少卿为吊祭使,出使南诏,又册立其子寻阁劝为南诏王,并铸“元和册南诏印”。元和十二年到十五年,南诏“比年遣使来朝”。因此,从铸“元和册南诏印”可以看出,元和时期唐与南诏的盟友关系仍然非产稳定。
总体来说,元和时期,唐与回鹘、南诏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和吐蕃关系得到缓和,大致处于和平状态。
三、民族关系状况对宪宗朝政策影响
元和时期,唐与诸民族政权处于相对和平状态,从而有利于朝廷集中力量平定藩镇。元和后期,吐蕃大规模寇边,朝廷不得不从东线调集军力加强边防(平定淄青时期)。但这时吐蕃显现衰弱,不具有更大威胁,平叛战争胜利局面也已基本形成,因此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唐在京畿用于边防的力量主要是神策军和缘边藩镇军。神策军和边镇军交错在一起,互相配合,共同防御。但在实践上,两者之间矛盾重重。首先在指挥上,京西镇军节度使要服从神策中尉,军情上报,决策下达,诸多环节,往往延误战机,“比得其报,虏已去矣”。神策军与边镇军也存在矛盾,神策军待遇优于边镇,也引起边镇军的不满。显而易见,制度上的问题消弱了边防力量,但宪宗并未积极行动,加以解决。在远离京畿的边镇,边防更为松弛,装备简陋,兵员散逸。元和八年,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求重修在元和七年被洪水损坏的东受降城。李绛、卢坦也认为此城十分重要,不应该吝惜费用,应该重修。但宪宗最终决定不再修理此城,而是将士兵迁移到天德军。天德军交兵之时,发现兵籍有四百,实际“止五十人而已,器械止一弓” 。1类似的边防松弛现象比较普遍,但当李绛罢宰相后,此事竟不了了之。
基于外部环境处于和平状态,边疆危机暂时缓和,宪宗在元和前期,政策上明显表现为重内轻外,更多的人力物力放在内部事务上。宪宗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平定内部藩镇叛乱,加强中央集权,并最终取得了“元和中兴”局面。总体来说,重内轻外政策适应了当时的具体形势,但是否完全妥当,还需进一步分析。
元和时期,唐与周边民族政权大体处于和平状态,但并不意味着边防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西边吐蕃控制河西地区,逼近京畿,对唐朝始终存在威胁。回鹘与唐朝在绢马贸易中摩擦不断发生,如果关系恶化,很有可能寇掠。当时人们也考虑到,如果回鹘“数道并进,何以遏之”。因此,边防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唐的内部事务。元和元年,征讨西川刘辟,朝廷征调神策军及边镇兵,李绛上疏,“吐蕃约盟未定,窥伺在心,间谍往来,急于邮传,又必持两端之计,与刘辟交通。若闻发兵西南,多取边镇,秋风即至,虏马已肥,冒隙乘虚必有侵轶。”元和四、五年,宪宗讨伐成德王承宗,白居易建言到,“臣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大小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伐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奴一一知之。忽见利生心,乘虚入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宪宗始终坚持对大局把握和既定政策,因此以上大臣建言,没有直接采纳。但边防问题存在却又是不争事实。元和五年,奚入寇灵州。七年,“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元和八年,“回鹘数千骑之鸊鹈泉,边军戒严。”因此,朝廷在平叛战争中又不得不考虑到边防问题。宰相李绛一向重视边防,其认为,“犬戎腥膻,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回鹘强盛,北边空虚,一为风尘,则弱卒非抗敌之夫,孤城为不守之地”。神策军主要用于保卫京畿及西北边防。元和时期规模较大的平藩战争有四次,既平西川、成德、淮西和淄青。其中,只有在元和元年讨伐西川和元和五年征讨成德动用了神策军。因此在实践上,边防问题制约着平定藩镇等内部政策实施。元和十四年,征讨淄青,期间吐蕃入寇,朝廷不得不把著名将领李光颜“徙邠宁军”,并且“以忠武兵从之”。
综上所述,元和时期,唐与周边民族政权处于和平状态,边境危机缓解。相对以往,宪宗朝可以更为专心于对内平定藩镇,成就“元和中兴”。同时,边防问题虽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也仍然时刻存在,需要警惕,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唐对内部事务的处理。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