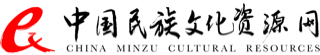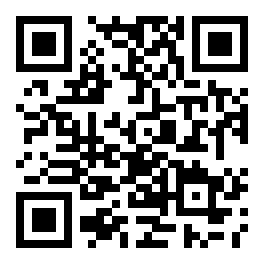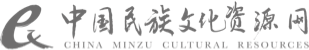幸福生活的文学书写 ——以央珍、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的小说为例
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族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得到了长足性提升。与此同时,西藏文学创作领域也涌现出一大批反映和表达西藏民众幸福生活的文学作品。
大致而言,民主改革以来西藏民众中的幸福生活书写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通过和平解放前后、尤其是民主改革前后,西藏各地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来展现新生活的幸福,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民众翻身做主,各方面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藏各族群众要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富起来”的生活追求,他们不仅追求经济的富足,同时也在探究精神方面的充裕,以及如何实现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步发展。文学的表达形态多样,表达类型丰富,也从侧面展现出西藏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藏族作家为主体的西藏作家群体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他们立足于西藏现实生活的坚实土壤,大胆创新、不断追求,用全新的眼光审视和展现西藏当代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代表性的作家有央珍、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等人。
1、
《无性别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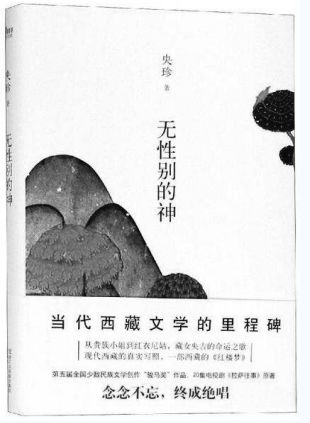
作者:央珍
出版单位: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修订版)
央珍:探究西藏女性对幸福生活的追索历程
央珍的书写着力探究西藏女性对幸福生活的艰难追索历程。她采用“平视西藏”的文学关注方式,从日常生活入手,以推己及人的文学思维方式,力图建构西藏女性的生活风俗画卷,塑造西藏女性的社会形象和文化地位。
央珍对幸福生活的书写起点是《卍字的边缘》,该作品曾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新人新作奖。“卍”字符号,在藏族民众生活中具有永恒幸福吉祥的文化意义,体现着藏族群众对幸福美满生活的企盼。央珍突破这一字符的日常象征藩篱,将生活中散乱的片段加以整合,创设出全新的文学意味。在这部作品中,女教师白玛和她的区长丈夫、麻风病院的夫妻俩都曾为了理想和使命走进大山,最终却并没有获得通常意义上的幸福。而城里“邻院的女人”,尽管“手上刺的卍在阳光下隐约显出”,却只能在情郎移情别恋后“发誓一辈子不嫁人”。央珍在作品中追问:为什么这些女性徘徊在幸福的边缘步履艰难?画在门上、刻在墙上、刺在手上的 “卍”在现实生活中真是遥不可及吗?对此,央珍陷入疑惑,并不断追逐生活中“卍”的印记而希望有所收获。
央珍的文学探索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城市知识女性的生活境遇出发,于1986年发表小说《阳光·小雨·月亮》;另一方面从乡村文盲女性的生活追求出发,探讨女性幸福生活的话题,在1987年发表了小说《羊肩胛骨上的卍》。前一篇书写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拉萨姑娘,屈从于母亲的传统生活方式而引发的对幸福的反思,艰难地跋涉在单调、孤独的情感世界中,甚至失去了追求幸福的勇气;后一篇则书写了牧童阿农的妈妈为了摆脱丈夫的溺爱、邻人的艳羡而获得生活的自立和自尊,毅然离开家庭到拉萨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两相对照或可发现,央珍真切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女性所承受的情感磨难,而挣脱情感枷锁实现精神自由,与知识的多寡并无直接的联系。
此后,央珍尝试着搁置现实生活而从精神层面来梳理藏族女性隐微的心灵结构,于1994年出版了小说《无性别的神》。这篇小说将目光投置在出生于贵族家庭而进入法门的小尼姑的杂乱而又惶惑的精神世界中,她徘徊于家庭生活的现实喧嚣与寺庙生活的精神纯洁之间,渴望家庭的温情与精神的飞升达成融通。在这篇小说中,央珍流露出无可奈何、无从选择的情绪,为此她采取了片段化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不断地将现实与回忆纠结在一起,缠绕出纷杂无序的情感世界的多样性,表达出在成长过程中的女主人公难以言说而又实实在在所感受到的精神世界的孤独与苦楚。而小说命名为《无性别的神》的原因,虽然央珍未曾言明,但通过小说中空行母的故事,暗示了神超然于性别之外,神是每一个人心中对于幸福生活企盼的象征,因此,幸福与否和性别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央珍回到历史探究层面,通过《无性别的神》中央吉卓玛的人生奋斗历程,表达只有女性幸福意识的独立自觉才能冲破现实的藩篱,才能最终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的观点。
2、
《放生羊》

作者:次仁罗布
出版单位:中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8月
次仁罗布:将目光投置于当代藏族民众的家庭生活
次仁罗布对幸福生活的书写,接续了央珍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步伐。不同的是,他更多地将目光投置于当代藏族民众的家庭生活,在对家庭伦理的日常关注中展现西藏民众的幸福渴望。
次仁罗布于上世纪90年代初登上文坛,他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文化语境已不同于央珍。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西藏的改革开放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念。不同地区的群众身处多种生活方式的裹挟中,既有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有现代的生活方式,还有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生活方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生活情态,次仁罗布展开了他对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探究。
次仁罗布的文学起点是小说《罗孜的船夫》。这部作品尽管在写作上稍显稚嫩,却表现出次仁罗布主动深度介入生活的文学品格。罗孜的船夫与其女儿以摆渡为生,生活平静而和谐,但康巴商人的出现打破了生活的安宁,引起了船夫女儿对外面生活的向往。或可言,罗孜的船夫是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康巴商人是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代表,船夫的女儿游离于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与康巴商人私奔后,面对现代生活的喧嚣与浮华,她又渴望传统亲情的抚慰。排斥现代生活的父亲拒绝进城,依然固守日益破败的田园牧歌生活方式。作品展现了当代藏族民众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幸福的艰难选择。
及至小说《笛手次塔》《焚》,次仁罗布关注了女性的出走问题,借此以回应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艰难追索。在《前方有人等她》中,次仁罗布将罗孜的老船夫的困惑通过夏辜老太太之口加以展现:为什么生活越来越好而人们的伦理道德走向滑坡?为什么传统的身体与心灵相谐和的幸福感在儿孙们的现代生活中难觅踪迹?
为了解答这一困惑,次仁罗布继续探索:首先,当人与自然遭遇,即便是人们遭受自然的无情嘲弄,但人们坚韧的意志和昂扬的斗志始终不屈于自然的淫威,如《雨季》中负重前行的农民旺拉;其次,传统的生活方式已不能束缚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婚恋、向往现代生活的步伐,如《传说在延续》中年轻人结伴走向城市迎接新生活;再次,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尽管能带来生活的变革,却难以抚慰人们之间渐疏渐远的心理隔阂,如《阿米日嘎》中美国种牛引入乡村,带来的只有纷争、怀疑,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最终,次仁罗布祭出了传统温情的大旗,暂时平息了风波。
这样的表述表达出次仁罗布对幸福生活的思考。尽管传统生活方式走向式微,但传统的伦理道德依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或者说是生发现代伦理道德的温床,他要在外在的现实生活的喧嚣中寻求心灵的安宁,以获得现时代的幸福生活。顺延这样一种思考,次仁罗布以《放生羊》表达出他的人生关怀。放生作为一种藏民族习以为常的生活习俗,表达出对生命的无限关爱和无限追崇。年扎老人与放生羊休戚相关的感情,昭示出次仁罗布的人生幸福的观念:只有心灵的恬适才是现代人生活最大的幸福,心灵的安宁能够弥补琐碎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张皇与困楚。
3、
《紫青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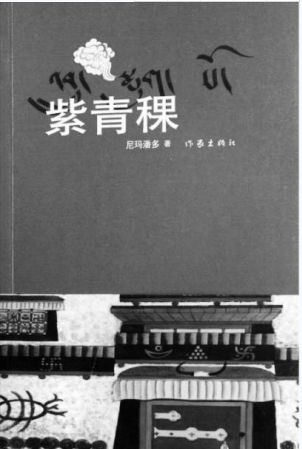
作者:尼玛潘多
出版单位: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9月
尼玛潘多:追索新生活方能获得新时代的幸福
不同于次仁罗布追求心灵世界的平淡与恬适,青年女作家尼玛潘多将目光投向乡村青年的奋斗历程。她认为,只有不断地追索新生活,方能获得新时代的幸福。
在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中,普村的青年男女们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尽管他们的祖辈安贫乐苦,习以为常,但年轻人要挣脱传统、亲情“脐带”的缠绕,希冀通过自我的奋斗实现命运的转变。尽管他们选择的人生路向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走向了城市。在城市中,他们孤立无援,都也激发出他们生存的本能;他们坚守着农民的操守,搏击生活的苦楚,最终实现了幸福生活的理想。
城市成了普村男女青年实现自我理想的奋斗之所,在农村中造就的勤劳、勇敢、拼搏、友爱的品格,成为他们融入城市、融入新生活的奋斗基底。尼玛潘多为西藏文学的幸福生活书写注入了新的活力,即奋斗者是幸福者,奋斗的历程就是走向幸福的历程。即便是挫折与失败,也彰显出他们不懈追寻幸福的奋斗品格。
由此来看,西藏民主改革60年,就是西藏各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60年。西藏作家们在民主改革一甲子的岁月中,立足于西藏的高天厚土,追寻着幸福生活的多种实现路径。幸福并不仅仅只是物质的富足,更是精神和心灵的自足,在奋斗中实现幸福,在时代的潮流中推进幸福的进程,在新时代的号角中追寻人生更大的幸福。而对于作家们而言,以其奋斗之笔书写新时代的幸福,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幸福。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