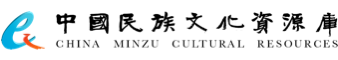

雾都起义领袖莫那·鲁道的后人林添喜在祖父生前唯一的照片前。李徽摄
“既然我们站起来反抗,我们就必须战到最后为止。这场战争,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现在不起来反抗,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后代将永远是奴隶!”
——莫那·鲁道
2010年10月27日,是台湾泰雅人分支赛德克人举行雾社起义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赛德克人不畏强暴,揭竿而起,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树立了一面旗帜。
雾社起义的爆发,并不是日本殖民者当时所说的是“蕃族”“出草”(台湾少数民族“猎首”的别称,指将敌人头颅割下的行为)的偶然事件,也不是以往所说的仅仅是为了减轻劳役、增加报酬。起义领袖莫那·鲁道在明知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必然失败,却义无反顾地率众起义,是因为这是关系到民族存亡、为了子孙后代不做奴隶的大事。
事件:惊天地泣鬼神
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属于台中州的能高郡(今南投县)。雾社一带世代居住着台湾少数民族泰雅人分支赛德克人,共有马赫坡、波亚伦、荷哥、罗多夫、塔洛湾、斯克等12 社(社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
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为掠夺这里的资源,上世纪初日本殖民当局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1930 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
1930年10月7日,赛德克人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为其儿子主持婚礼,日本警长吉村刚好路过这里,莫那·鲁道的儿子达拉奥·莫那便给吉村敬酒。吉村见达拉奥手上有杀猪留下的血迹,就故意刁难,并挥手杖打莫那·鲁道。达拉奥见父亲受辱,便当众把吉村揍了一顿。日警当局出面干涉,扣留并毒打莫那·鲁道,他的儿子便联合同族青年杀死了吉村。莫那·鲁道知道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便联络了马赫坡、罗多夫、波亚伦、斯克、荷哥、塔洛湾6社,于10月27日共同起事。是日,驻扎在雾社一带的日本人集中到雾社公学校操场举行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拂晓前,莫那·鲁道等人分头行动,切断了电话,破坏了交通要道,随后袭击各社日警据点,杀死日本警察,夺得武器。上午八九时,当运动会升旗仪式举行一半时,达拉奥等人突然冲进运动场,砍下了台中州“理蕃”课顾问管野政卫的头。义军从四面八方冲入,共杀死日本人134人,伤250人。
起义消息传出,一时震动台湾全岛。日本台湾总督石冢英藏立即发出“讨伐”谕告,从台北、新竹、台南等地调来大批军警,“围剿”起义民众。10月29日,雾社被攻克,起义部队分成两线退守,莫那·鲁道率领其中一线于31日在马赫坡社与日军对决。11月2日,马赫坡社被日军占领,起义部队退入山中苦战。为了避免消耗粮食,让勇士无后顾之忧,妇女们带着幼童一齐上吊自杀。12月初,对日作战已经超过40天,勇士们陷入饥寒交迫、弹尽援绝的窘境,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在断崖上持枪自杀。在长达两个月的起义中,雾社人民被炸死、毒死、枪杀或自杀的,达700余人,占雾社总人口的58%。
雾社起义4年后,莫那·鲁道的尸体被狩猎的群众发现,日本人遂将其送到台北“帝国大学”当做人类学标本。1973年,台湾当局将其遗骸迎回雾社安葬,并建雾社起义碑,供世人缅怀。
原因:为了尊严与生存
1898年,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由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虽然日本殖民者常把“内(指日本本土——引者注)台一体”、“一视同仁”挂在嘴边,但实际上,正如自1898年至1906年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所说,日本人仍视日台“有别,渐谋同化而后可”。
当时,日本殖民者把居住在台湾的人分成三等,实行差别待遇:一等是日本人,二等是台湾的汉族人(日本人称为“本岛人”),三等是“蕃人”(台湾少数民族)。他们从事同样的工作,所得报酬却是不同的。比如,都是乙等巡查,日本人的工资是65元,“本岛人”45元,“蕃人”只给35元。当地的初等教育也分成三种:“小学校”的师资力量最强、设备最好,只招收日本儿童;“公学校”的师资和设施都很差,专门招收所谓“本岛”儿童;专收“蕃族”儿童的又称“蕃童教育所”,由日本警察兼任教员,根本就没有什么教育设施。日本人对台湾儿童的教育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后藤新平所说的“以普及国(日)语为目的”。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处处散布民族歧视的言论,“生蕃”、“野蛮”、“愚昧”就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词汇。为了加强殖民统治,日本殖民者还对台湾少数民族实施不同于日本国内甚至岛内汉族的法律。日本国防大臣松田原治曾说,对于“蕃地”来说,“在本国(日本——引者注)所施行的法令是不适用的”,“历代的内阁都没有将此文化人的法令施于蕃地。”松田原治公然宣称日本人是“文明人”,“蕃人”是要日本人“教化”的“极蒙昧愚鲁”的人,因此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日本殖民者正是用自己的诡辩和所作所为,戳穿了自己是民主时代“文明人”的谎言。
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时代,台湾少数民族没有基本的人权,没有行动、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在日本人看来,“蕃人”的文化程度过低,不能在公法和私法中享受“人”的待遇,不能适用“人”所适用的法规。在“蕃地”,日本殖民者实行包括《枪炮火药取缔规则》、《蕃务监视规程》、《官有林野取缔规则》、《五年讨伐计划》、《蕃地取缔规则》以及“违警例”在内的“理蕃”政策。赛德克人在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时曾说,他们连交易农作物都得经过日本人,到集镇里更是要受到他们的控制,“真是一点自由也没有”。
日本殖民者还使用种种卑鄙手段,实施民族同化政策。比如,在“蕃童教育所”,警察教员要求学童只能说日语,禁止讲赛德克人母语和汉语;不准赛德克人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禁止赛德克人黥面;对“出草”的人处以极刑等。日本殖民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被统治民族的一切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以“大和民族文化”为标准,在台湾建立起日本的“皇国文化”。
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这里的自然环境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与赛德克人敬畏森林、爱护森林的传统分不开。传说,雾社赛德克人的祖先是在一颗圣树中诞生的。人死后,灵魂会回到森林中的圣木里去。因此,森林就是赛德克人的圣地,森林中的巨木就是赛德克人的守护神。1929年到1930年,日本殖民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赛德克人到森林中砍伐巨木,引起大家的畏惧和不满。莫那·鲁道曾代表族人与日本警察交涉。他说:“桧木是我们祖先之灵的所在,砍伐了这些圣树,神一定会发怒的。圣木被砍倒以后,谁来保护我们呢?砍伐圣木是逼着我们虐杀自己的神。没有圣木,也就没有了雾社的精神,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狩猎是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猎物是当地居民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削弱反抗力量,1904年5月,台湾总督府公布了《枪炮火药取缔规则》,严禁民间私藏枪炮火药,收缴各类枪械2.7万支,他们还与猎民约定,打猎时可以向警察借打猎专用的枪支弹药。但日警不信守承诺,有时一个部落只能借到一支枪、一发子弹,有时什么都借不到,赛德克人的食品获取因此十分困难。
日本殖民者“理蕃”的目的,一是为了同化当地居民,二是为了掠夺当地的土地、森林资源和其它物产。台湾盛产樟脑,当时年产量约2500吨,相当于世界总产量的70%。日本在占领台湾的第二年(1896年)就公布了《樟脑规则》,次年公布《樟脑油规则》,随之又实行樟脑专卖制,控制着台湾樟脑的产销。
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所谓的“林野调查”,把大片山林攫为官有。以三井、三菱为首的日本财团也肆意霸占山林,侵吞良田,破坏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日本国会众议员河野密在1931年发表的《调查雾社事件的真相》一文中指出:“对蕃地收夺,缩小了蕃人的生活范围……过去数次讨伐,蕃域缩小,蕃人赖以为生的狩猎区也因此狭窄。因此蕃人的生活愈加陷入困境,这都是事实。……尤其对迈勃(即马赫坡——引者注)森林的采伐,迈勃社蕃人认为这是直接的掠夺。”不管河野密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到雾社进行调查,他的话都揭示了日本殖民者疯狂掠夺山地资源的状况。
1930年的雾社起义被日本殖民者使用机关枪、大炮、飞机和毒气弹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起义戳穿了日本殖民者通过实行“理蕃政策”造就了“模范殖民地”、“模范蕃地”的谎言,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以莫那· 鲁道为首的英雄们为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而起义的壮举名垂青史。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