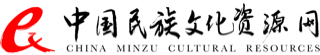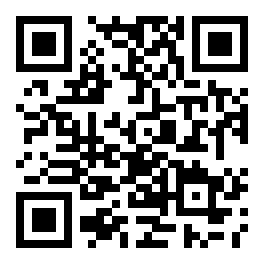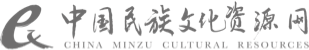《我不是药神》:中国电影的 “运”与“势”

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15天,票房已经达到26.5亿。李克强总理近日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我不是药神》火爆的突发性、公众关注度及持久性,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爆款”。如果说《战狼2》的火爆来源于影片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家国情怀表达契合人心,那么,《我不是药神》则打开了当下中国电影的另一个社会心理爆发点:现实主义的民生体验与诉求。
《我不是药神》最触动观众的是“看病难”。它涉及到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但这只是表面,真正触动观众的是全球化图景中中国普通人的安全感隐痛和焦虑。影片中的反派是跨国药企的代表,他们利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维持着白血病特效药的高昂药价。资本的本性使药品用途异化为逐利工具,而与救治生命无关。影片中作为国家形象的警察、法律系统一开始也出现了主体性迷茫,作为跨国药企利益的维护者出现。跨国药企代表颐指气使,甚至在警察局追查走私药品的办案现场指手画脚,暴露了全球化社会中资本的霸权地位。好在影片最后用国家出场纠正了全球化潮流中国家价值观的偏离,遏止了人道主义灾难。
影片中,主人公从印度输送白血病患者的廉价救命药,沉浮在具体真实的全球化商业社会中。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也呈现出如印度一般的“第三世界”属性,这种影像在当下中国电影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主人公所在的上海,不再是流光溢彩的全球化大都会,而是以最普通、甚至有点不整洁的小街道面貌出现。影片所展现出的普通患者艰难求生中的喜怒哀乐,在主流影像里也是罕见的。
近年来,中国主流商业电影院线里,商业片或崇尚奢华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或宣导一种小资的生活态度;而文艺片则多采取精英的启蒙主义态度,传递一种符合全球化议题设置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现实主义在当今主流影像里不再是主流,《我不是药神》则重新挖掘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艺术传统的潜力。
尽管电影中隐约可见韩国电影或好莱坞电影的某些戏剧性套路甚至剧情结构。比如在主人公周围的几个白血病朋友,包含着牧师、舞女、小工等,分别对应着宗教、女性、农民等社会形象,概括出多样性的社会群体,展现了多样化的社会面貌。但是电影没有落入“景观化”的窠臼,各种景观中潜伏的是作为中国人的真实生命体验与愿望,也隐藏着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在全球化潮流中的真实处境。
影片中,主人公作为落魄英雄,利用从印度贩卖假药,捞到了第一桶金,本来已摆脱困顿,适应了当下经济社会规则并与之浑然一体。但往日白血病朋友的求助让他猛然看见了生活的真相,促使他重义轻利,找回了自己的世界观。主人公的形象及其改变,正是中国作为当代民族国家的隐喻,他的觉醒与奋勇实践,与电影结尾时国家的改变,可以看成是一种对应。事实上,结尾字幕中出现的国家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也不是主旋律式的附会,而是作品结构组件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的“医”与“药”,就像当年谢晋执导的电影《春苗》一样,都具有社会隐喻性,指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疾病。《我不是药神》也诠释了中国在全球化路径选择中的自觉自省。
近几年,我国电影“爆款”越来越多,也许一个“爆款”会被看作是文化的孤例,一阵喧嚣之后,再大的“爆款”也会被重新淹没在主流影像里,其革命性意义也会被消解。但一个“爆款群”的出现说明,社会思想正处于活跃的状态,而观念的生产与激发也越来越频繁。这还是要归结为中国当下主流电影的某种“文化转型”,它是对以往电影市场的文化成规和秩序的某种超越和修正。“爆款”所引起的商业追风,以及电影美学的改变,将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使电影界固有秩序中的行业精英们受到来自文化与商业的双重压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其所建构的商业常识系统也越来越趋近落伍。一个又一个“爆款”激起的公共性讨论,正在启发中国电影新的“运”与“势”。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