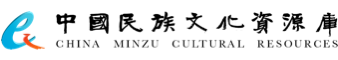

《康定情歌》剧照
01
四川藏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约占四川省总面积的51.49%,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不同的族群在这条 “民族走廊”内迁徙或定居、交汇或融合。自7世纪西藏吐蕃政权一度征服这一地区后,藏文化开始向这一地区的传播和渗透,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藏族文化圈的一部分。
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带。四川藏区处于青藏高原向内陆台地过渡地带的横断山区,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之间的板块运动导致该地区地质活动活跃,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频频发生。
在川藏,城市的发展长期与自然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原乡土著们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积累了大量应对自然灾害的机制。自18世纪中央政权加强对四川藏区的统治后,川藏地区的城市愈来愈受到内地文化的影响,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张开怀抱,积极主动地迎接地质灾害的挑战。
诸多的城市中,康定受汉地影响更大,表现出很多不同的应对方式,如城市迁移,用木结构穿斗房取代部分碉房,改变城市空间等等。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
1946年,一个马夫哼唱的一首《溜溜调》旋律吸引了当时的音乐文化教员吴文季,于是他整理、改编、加工后,便诞生了如今享誉世界的《康定情歌》,这首歌最早的名字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
就让我们跟着悠美的歌声,重回康定去……走一走吧。
02
一些传统聚落作为宗教中心、贸易交通枢纽、军事要塞或土司官塞得到发展,成为最早的城镇,甘孜州的首府康定便是其中发育较早的城市之一。
康定在交通上的重要位置使其成了“汉藏交通枢纽”的不二之选,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治藏之“依托”,控驭藏地之“锁钥”。
康定城不同于平原城市,起伏的高原面与深浅河谷共同制约着这一片土地,使这一地区的城市在发展上不可能“为所欲为”。
康定城位于三山夹峙的河谷地带,折多河由南向北穿城而过,数百年来康定城一直沿折多河两岸发展,由简单的聚落,发展成为“Y”字形的山地枝状城市。整个城市的建设用地形似树枝,延着河谷生长开来。
在地质条件上,康定位于四川地震史上最为活跃的一条地震带——鲜水河地震带上。据统计,自1725年以来,康定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共4次,对城市造成严重破坏。
“1725年8月,7.0级地震,当地衙门、民居、碉楼全部倒塌;1786年5月,7.5级地震,城垣全部倒塌,文武衙署、仓库、兵房共塌169间,城内店铺房屋倒塌722间,土房54间,藏民碉房177座;1792年11月,地震,城垣倒塌,碉房震倒数百间;1923年,7.5级地震,当地居民死亡约1300人,城垣倒塌,周边山石倒塌;1955年4月,7.5级地震,城乡倒塌房屋共600余间,裂坏500余间。”
——来源:《康定县志》
03
康定最初的形态与发展与大多数早期藏族聚落一样,它最早是部族的夏季草场,几乎无人居住, “自唐以来,随茶马交易,日趋繁盛”。城镇形成初期,住房多为石块所砌碉房,交易场所为临时性锅庄帐幕。
在选址上,四川藏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聚落选址的意义格外重要。
聚落一般围绕着寺院发展,而寺院最初的选址则要经过复杂而仔细的地质考察,择取“风水地貌圆满之地”建寺,城镇中土司官寨、居民住宅的择址都要由寺庙的指定喇嘛进行指导。
和大多藏区城镇聚落一样,康定城最初的择址面朝南方,日光充裕,靠山面河,具有避风、近水、靠近树林的特点。城里最初仅有十几家民居围绕着土司官寨与喇嘛寺形成聚落。
这些建筑作为传统藏式建筑,均以当地的泥土、石、木材为原料,主体结构依据材料和地质状况来确定。
传统藏式建筑的主体结构类型主要有墙承重式“崩空”、梁柱框架式、内框架墙柱混合承重式三种类型。
“崩空”是圆木或半圆木榫卯咬接垒叠而成的井干式木屋。这种墙承重的“箱型”房屋整体性好,但规模受到木材尺度限制,一般用作独立房间如贮藏、卧室、经堂。通常人们将“崩空”放至其他结构的二层或顶层局部使用。
梁柱框架式为竖向列木柱,柱头设置替木承大梁,梁、替木与柱头交接处开设榫卯连接。梁之上水平平行密铺木檩,再铺枝条、柴棒,覆土打实(楼层铺设木地板)形成屋面。柱列外围砌筑不承重的土、石围护墙体。
而内框架墙柱混合承重式是先以石块砌墙,留门窗洞,然后在墙上架梁搭椽,铺盖瓦板或石板即可;或是先作简易木构架,再以石块砌筑,建筑以石墙承重。
当地的特殊气候条件需要建筑注重蓄热、保温、防风性能,促成了平面方整紧凑、墙体厚实、对外封闭的平顶建筑形式。
梁柱框架式建筑形式在四川藏区较为普遍,但在各地边柱外砌筑围护墙体有所不同,因康定地处河谷,石材丰富,多则以片石砌筑墙身。
从文献记载看,康定初期城镇建筑多为一、二层夯土密梁平顶式。经多次地震灾害后人们也在逐渐摸索增强结构刚性的经验,出现了在内部或上层墙身做井干式木墙的做法,减轻自重并加强相互间的撑托。
一些建筑开始探索采用框架与“崩空”结合的混合式碉房,在二层角部或间隔设“崩空”房,框架柱间填井干式木墙与立柱榫卯镶嵌形成灯笼框架。
除了在建筑形制上适应地质条件外,四川藏区盛行的藏传佛教也使这一地区的人们对待地质灾害有着独特的理解。
藏民认为人的死亡如同出生一样,是生命中一件普通事件。对于多灾多病,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来说,认识痛苦、承认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
具有深厚人文关怀的心灵慰籍使藏人总是平静地接受自然给予的一切。
1870年在藏区城市巴塘发生7.5级地震,造成包括当地土司,四百名喇嘛在内的约二千名当地居民死亡,上海的英文媒体《North China Herald》报道了这一灾害,报道认为坚定而柔韧的宗教信仰给了藏区民众在灾害中重生的勇气和坚强的承受能力。
我们看到,藏区土著民众有着对抗地质环境的传统经验,这些经验更多以被动而柔软的方式寻找到人类在自然中生存的方式。
04
清代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将边疆地区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行政建制中,通过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强化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康定作为四川藏区的地区中心城市发生了很多变化,而其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也伴随着其内地化的进程而发生变化。
清康熙五年(1666年)清政府开始通过“重新认定土司”,清理四川藏区的统治秩序。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政府取得了战争胜利后,重设明正土司以统治康定地区,设关卡,派官员监督征税及贸易。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正式在康定设置代表中央的地方政权机构——箭炉厅,作为地区统治中心,并于次年派驻军队驻扎在城市中。打箭炉很快成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的贸易重镇。
乾隆十年(1745)明正土司也由木雅驻地迁居康定城内,兴建土司衙门及安置其重要下属——18家土目的庄房,作为他们在城内支差侍贡时住宿之用,同时先后在城内外建了七座喇嘛寺。
在康定迅速发展近40年后,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打箭炉这座城市经历了重大的自然灾害。在连降大雨数天后,跑马山山上湖水崩溃,随后整座城池被泥石流冲毁,化为石滩。城市损失惨重,城中铺户仅存十之一二,当时的四川总督文绶亲赴康定查勘灾情。由于康定对中央政府推行藏区政策的重要性,清政府专门下旨,要求城市易址重建,选址到更为安全的跑马山脚下,离开河滩地区。
“新城沿折多河两岸发展,交通更为便利,依山沿河而建,参差错落,街道线型弯曲,以减缓山谷风势。为方便两岸群众交通往来,建有廊庭式桥梁4座。城镇除河东、河西两条主街和连接4桥的短街为石板路面外,其余街巷均为鹅卵石铺路。”
——来源:康定档案馆《打箭炉志略》
18世纪中期前康定旧城位于今公主桥一带,修建有城门及城墙。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旧城毁于泥石流灾害,城址移至子耳坡背水处新址。乾隆五十一年大地震后,一些城中建筑改建为穿逗木结构的楼房,城市沿河道发展。
05
康定城内中的建筑最初以喇嘛寺庙、碉楼、官塞等为主,建材主要用石块、木材、黄泥等材料。城中到处是几米乃至十米高的碉楼等建筑物,棱角分明,线条清晰而规整,表现了藏族工匠的精湛技艺。
随着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汉文化的输入,特别是地质灾害带来的影响,建筑风格与用料逐渐渗和了汉族风格。
据康熙五十九年的游记记载,当时的康定城里有许多汉族移民和官员,但城市仍像个村庄,城中房屋与藏地其余房屋一样,仍以碉房和帐篷为主。但到20世纪初,康定已是由许多木结构房屋组成的城市。
数次地震灾难使石砌碉房这一传统建筑技术受到挑战。在史书记载的数次地震中,碉房在地震中倒塌带来的严重伤害使人们印象深刻。
在1725年8月1日的地震中,城内喇嘛寺院、官员住居衙门、平民楼房俱行摇塌,一间无存,百分之八十的商人和居民被楼房压死,其中包括当时地方最高长官土司桑结、驿丞俞殿宣、料理钱粮事务的典史徐中宵。
1786年的地震中,砖石城墙倒塌,文武衙署、仓库、兵房共塌169间,城内店铺房屋倒塌722间,土房54间,藏民碉房177座。
经过乾隆年间数次大地震后,康定随后重建的官衙住房、商贸民房、坛庙会馆、回族清真寺、先后由碉房建筑多改为穿逗木结构的楼房。基本上所有的城区居民住房在民国时期都逐渐由抗震效果更好的木结构代替了原石砌碉房。民国时期康定城内多为穿斗木结构一楼一底小青瓦屋面低矮房屋,但与内地住房有所不同,为防火灾,部分房屋两侧或后建出屋面石墙围之,称为风火墙。临街房屋均于楼层支出0.8米左右的吊脚楼。
但这些住房在汉化的同时仍保留着明显藏地民居特点,很多住房在正房后建有一小房,仍象过去的碉房一样四面围以高出屋面约2尺长石墙,门用厚木板包上铁皮做成,俗称“土仓库”,用以存放家庭贵重物品,既防火防盗,又防兵变抢劫。
康定的建筑工匠最早是由藏区内的阿坝和丹巴等地来康地的技工组成,称为西路帮,他们擅长以石块砌墙,是砌乱石墙能手,不用挂线角尺,能砌成墙面平整,棱角四现,块石交错叠砌之墙。
清中叶以后,来自四川的内地工匠成为了建筑市场的主力,他们更长于木结构及砖木结构的建筑技术,可见康定城市内建筑风格已发生变化。从汉区来康定的匠师,针对康定城地窄面小、风大、火灾多、地震频繁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改建出抗震性较强的穿斗木结构低矮小楼房,加风火墙及附属的碉房似平顶“土仓库”。
06
早期的康定只有寺院,锅庄,城门等少数公共空间可以提供给人们交流、交易。近代以来,城市广场空间出现于康定。
早期康定城的城市广场位于礼堂前侧前空坝子,空间较小,现在这个广场经重新设计建造,成为三面围合式广场,不仅为城市提供了休闲、娱乐、交流的公共场所,也提供了地质灾害中的城市避险场所。
早期康定城市布局毫无规划,居民商户都各自沿街圈地建房,导致街道窄小多弯,布局极不合理。随着城市的变迁,早期自由发展的街道无法满足后期人们的使用,1933年城市开始加宽街道马路,一般加宽至4米,过于狭窄的地方至少加宽至3.3米,并为此进行了一次拆房加宽的运动。此次拓宽马路还明确规定了人行道的宽度为0.6米至1米。
1943年,康定又将城市主干道加宽到六米。公共空间及街道的改善改变交通状况的同时也有利于城市避灾抗震。政府也试图通过控制建筑密度和增辟公共绿地,减少地震带来的危害。因此康定城不断向两侧扩大延伸。1949年后的康定城市规划希望以“控制、改造、疏散、发展”为指导思想,针对康定地质状况发展城市建设。
07
康定城市生长过程一直受到多发地质灾害的影响,一次次地质灾害后的城市的重建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当地质灾害粗暴地中断城市的发展,破坏原有的城市物质形态与正常的功能时,城市在重建中所做出的选择是我们研究城市的最好切入点,它们反映着城市当时的价值体系,影响着未来的城市建设。
我们发现,与藏区其它城市相比,受内地影响更大的康定更为主动的迎接地质灾害的挑战,其城市空间与建筑在重建中一次次得到更新。除了延袭原乡土著原有的生活经验外,康定城也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思维方式,丰富了应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机制。
- the end -
注:
本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51108379):“内地化进程中的四川藏区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研究(1640-1968)”。
作者:田凯,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陈颖,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